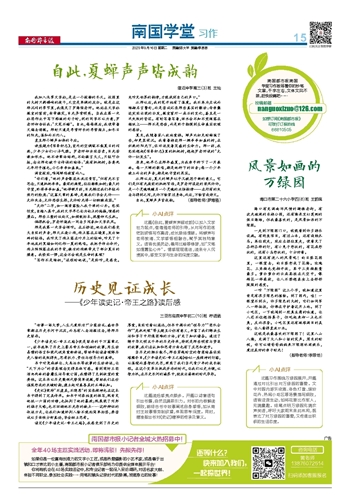澄迈中学高三(3)班 王灿
我加入浅草文学社,是在一个寂静的冬天。校园里的大树只剩嶙峋的枝干,天空是单调的灰白。就是在这样沉闷的季节里,我遇见了罗海强老师。他站在文学社教室的窗前,面带微笑,目光异常明亮。当我在第一次社团作业中写下稚嫩的句子时,别的同学不以为意,罗老师却告诉我:“文笔不错”。自此,每每课后,我便带着文稿去请教。那时只道是寻常师长的寻常指点,如冬日的阳光,温和而不灼人。
直至那个蝉声如沸的午后。
讲座题为《项脊轩志》,室内的空调驱不散夏日的闷热,少年少女们心浮气躁。罗老师却安然若素,目光澄澈如秋水。他不讲章法结构,不论微言大义,只轻叩白板,念出那句被千古传诵的结语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
满室寂然,唯闻蝉鸣破窗而入。
“你们看,”他的声音像溪水流过青苔,“归有光不言思念,只道枇杷亭亭。最深的痛楚,往往静默如树;最久的守望,终将亭亭如盖。”他停顿片刻,目光拂过我们年轻而焦灼的脸庞:“这篇文章的真谛,是教我们学会允许——允许失去,允许悲伤生根,允许时光将一切酝酿成荫。”
“允许”二字,如一滴清露坠入我干涸的心井。忽然惊觉,自踏入高中,我的文字早已沦为论点的傀儡,情感的赝品。那些工整的议论文,如精致标本,规整却无生机。
偶得机会,罗老师邀我一同去乡间参加文学采风。
那是我第一次学会倾听。在石桥边,他让我们感受大自然的声音,那天正逢小雨,雨点落在石缝里,发出细碎的轻语。我听见了雨点落在叶片上的轻响,听见了十年地底的黑暗如何化作一夏的绝唱。我把手伸出伞外,雨点悄悄落在我的手背,微凉的雨珠带走了部分夏日的燥意。我倏然一愣,这会不会就是生命的真理?
“写作不是堆积,”返程时他说,“是聆听,是感受。先听见世界的韵律,才能找到自己的声口。”
从那以后,我的笔开始有了温度。我不再为应试而堆砌名言警句,而是尝试记录那些真实的颤动:母亲鬓边突然出现的白发,教室窗外一朵云的变化,甚至是一次失败的苦涩。有时写着写着,泪水会不知不觉滴落在稿纸上——那不是悲伤,而是终于触摸到生命真实纹理的感动。
夏末,我随着家人故地重游。蝉声比初见时稀疏了些,却更显深沉。我看着湖边那一棵亭亭如盖的树,在炽热的阳光下,依旧迸发着茂盛的生命力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《项脊轩志》里的枇杷树,想起罗老师说的“允许一切发生”。
原来,他早已在那年盛夏,为我亲手种下了一片森林。每一只蝉的歌唱,都是他种下的回音;每一个少年破土而出的声音,都是他守望的果实。
从那以后,夏天的蝉声似乎又被冠于新的意义。它们是归有光庭前的枇杷絮语,是罗老师溪边的清风许许,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永恒韵律——在所有的失去与得到之间,允许万物穿过身体,而后,万物皆成诗文。
自此,夏蝉声声皆成韵。(指导老师:罗海强)
小AI点评
这篇《自此,夏蝉声声皆成韵》以加入文学社为起点,借海强老师的引导,从对写作的迷茫到领悟写作真谛,成长脉络清晰。将蝉声与老师教诲、文学感悟相融合,赋予其独特意义。语言优美灵动,善用比喻等修辞,如“文笔如清露坠心井”。情感层层递进,读来令人沉浸其中,感受文学与生命的深度交融。